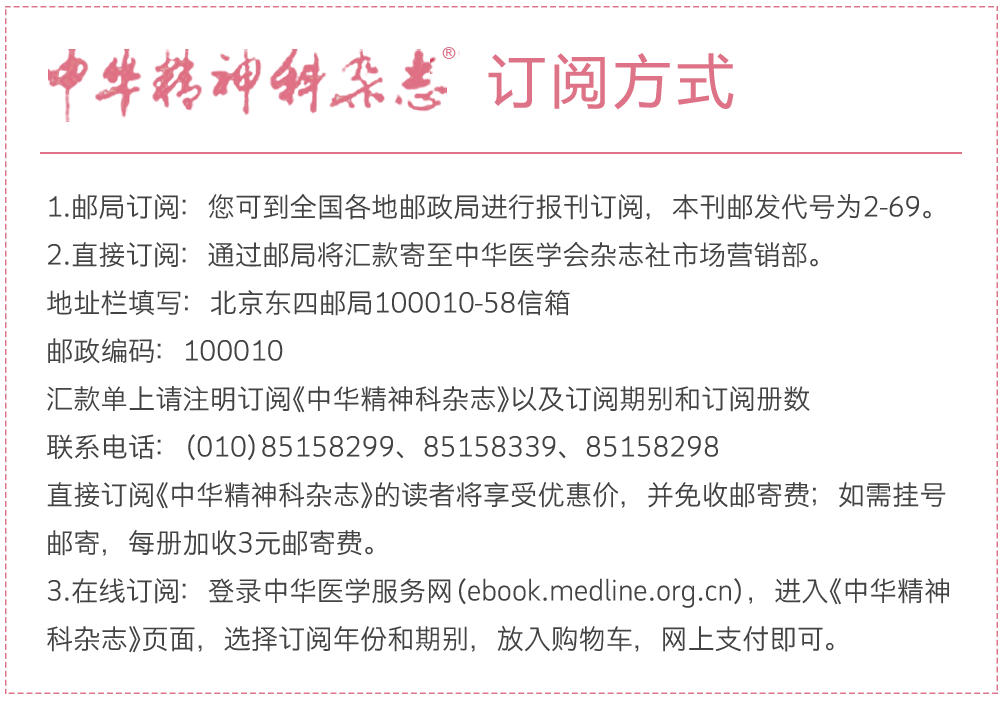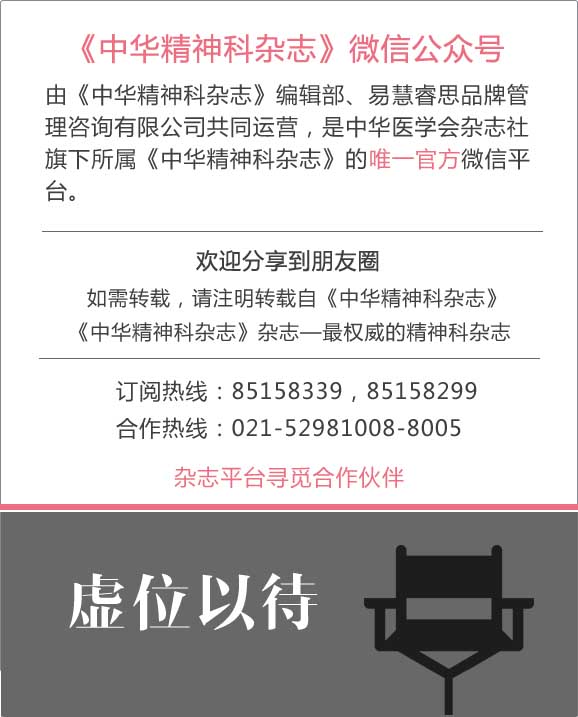多巴胺与精神活动
2019年4月
中华精神科杂志,第52卷第4期 第287页-第289页
赵靖平,孙梦夕
多巴胺是中枢神经系统内重要的神经递质之一,参与调节多种精神活动,包括心境、认知、动机、运动功能、冲动与愉悦感等。
大脑内有4条已非常明确的多巴胺通路和1条新近发现的多巴胺通路。前者包括中脑边缘通路、中脑皮质通路、黑质纹状体通路和结节漏斗通路,而新通路的神经分布在丘脑[1]。(1)中脑边缘多巴胺通路:从中脑腹侧被盖区发出投射至伏隔核,是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被认为与许多精神活动与心理功能有关,如快感、药物滥用的强烈欣快感以及精神病的妄想和幻觉。涉及了情感与行为的调节,并被认为是调节精神病阳性症状的主要通路。尤其认为该通路的活动过度引起妄想和幻觉,是经典精神分裂症多巴胺假说的基础。(2)中脑皮质多巴胺通路:从中脑腹侧被盖区发出投射,但却将其轴突送至前额叶皮质区,认为这条通路到背外侧前额叶皮质的分支调节认知和执行功能,而到前额叶皮质腹内侧部分的分支调节情绪和情感,它们可能起着介导精神分裂症认知症状(背外侧前额叶皮质)、阴性症状和情感症状(腹内侧前额叶皮质)的作用,是精神分裂症阴性、认知和情感症状的中脑皮质多巴胺假说的基础。(3)黑质纹状体多巴胺通路:从黑质发出投射至基底神经节或纹状体,是锥体外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控制着运动神经的功能和运动。其病变可导致帕金森病,以震颤、僵硬和运动减少为特征。黑质纹状体通路的多巴胺过度活动被认为是许多运动机能亢进性运动障碍(如舞蹈症、运动障碍和局部抽搐症)的基础。此通路多巴胺D2受体的慢性阻滞可引起一种运动机能亢进性运动障碍,称为抗精神病药所致的迟发性运动障碍。(4)结节漏斗多巴胺通路:从下丘脑发出投射至垂体前叶,控制着催乳素的分泌。抗精神病药阻滞多巴胺D2受体,会引起升高的催乳素导致泌乳(乳腺分泌)、闭经(不能排卵和月经周期紊乱)以及其他问题如性功能障碍。(5)第5条通路出现于多个位点,包括水管周围灰质、腹侧中脑、下丘脑核群以及臂旁核,发出投射致丘脑。其功能目前还不清楚。
中枢神经系统的多巴胺功能由5种G蛋白偶联受体介导,依据生物化学和药理学性质,这5种多巴胺受体可分为D1样受体(包括D1R和D5R)和D2样受体(包括D2R、D3R和D4R),他们在信号转导、结合谱和生理效应方面的功能存在不同。D1样受体主要与激动性Gs蛋白偶联并增强腺苷酸环化酶的活性,而D2样受体主要与抑制性Gi蛋白偶联并抑制腺苷酸环化酶的活性。多巴胺能受体的配体很容易区分D1样和D2样受体家族成员,但是却难以区分同一家族内的成员。例如,D1受体的拮抗剂和激动剂对同一家族的D1和D5受体有相似的亲和力。目前研究发现D2受体与神经精神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关系密切,因为D2受体是所有抗精神病药和治疗Parkinson′s病的多巴胺激动剂的结合位点,所有抗精神病药都作用于D2受体。而D1、D3或D4受体与抗精神病药的作用以及与精神分裂症临床症状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
中脑多巴胺能系统负责奖赏机制,该机制强化了生存必需的行为,包括食物摄取和性活动。多巴胺功能紊乱是物质成瘾性疾病的生理学关键因素,几乎所有的成瘾性物质都会直接或间接升高伏隔核突触间的多巴胺水平。中脑腹侧被盖区与伏隔核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是奖赏的关键神经环路,称为奖赏中枢。背侧和腹侧纹状体中,多巴胺D1受体和D2受体在运动控制和奖赏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3,4]。
甲基苯丙胺是一种成瘾性精神兴奋剂,滥用后会导致注意力、学习能力、记忆力和执行功能受损。甲基苯丙胺诱导的单胺类神经毒性持久。动物实验显示,通过纹状体使用多巴胺D1受体或D2受体拮抗剂可使甲基苯丙胺诱导的纹状体内单胺类递质减少并改善认知缺陷[5]。分裂症断裂1(DISC1)基因缺陷小鼠改变了纹状体中多巴胺D1受体介导的信号,表现出可卡因诱导的过度运动,并且阻断多巴胺D1受体可抑制这些表现;提示DISC1基因的缺乏可通过突触后D1受体增强可卡因诱导的多巴胺信号[6]。
Scuppa等[7]在大鼠MRI研究中发现,酒精依赖史改变了大鼠静息态大脑连通性,在显著网络中,岛叶和扣带皮质之间的联系减弱,岛叶和中脑边缘奖赏系统之间的联系增强。重要的是,急性给予选择性多巴胺D3受体拮抗剂SB-277011-a可部分恢复酒精依赖后大鼠的异常大脑联通性。因此,所有物质成瘾障碍与腹侧纹状体多巴胺释放有关,阻断多巴胺受体能改善物质成瘾症状与复发。通过基因敲除与降低动物(中脑腹侧被盖区与伏隔核)多巴胺水平,以及拮抗多巴胺的治疗都证明了多巴胺功能障碍是物质成瘾的重要生物学机制之一。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特征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情绪增加,约5%的学龄儿童受其影响。ADHD通常与其他精神障碍共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物质使用障碍等,这使其诊断和治疗复杂化。对ADHD儿童的纵向随访研究和基于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估计,多达三分之二的ADHD儿童成年后依旧表现出ADHD的症状[8]。
多巴胺系统与ADHD的病因学和药物治疗关系密切。基因水平研究发现多巴胺D4、D5受体基因多态性和多巴胺转运体基因多态性与ADHD关联。多巴胺神经元突触前膜上的多巴胺转运体功能亢进,使突触间隙的儿茶酚胺回收过多而儿茶酚胺的浓度下降,是ADHD的主要发病机制之一。ADHD的治疗药物哌醋甲酯或D-安非他明是精神活性化合物,与脑内儿茶酚胺神经递质相似,通过兴奋多巴胺的功能而改善多动与注意力障碍等症状。D1受体激动剂也可通过促进多巴胺释放使ADHD患者得到帮助[9]。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精神活动与环境不协调的重性精神障碍,其特征包括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障碍。多巴胺假说认为阳性症状与边缘多巴胺D2受体的过度活跃有关,而阴性症状与前额叶D1受体传导的低活性有关。
精神分裂症患者最有力的神经化学异常证据之一是纹状体背侧的多巴胺合成和释放增加。随着患者从前驱期发展到精神分裂症,多巴胺似乎也随之增加[10,11]。最近有PET研究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放射性标记的左旋多巴(多巴胺前体)摄取增加,纹状体中多巴胺的释放增加,并且左旋巴多摄取增加与患者的治疗差相关[12]。Petty等[13]使青春期大鼠纹状体背侧中多巴胺合成能力增加,成年后模型大鼠在低剂量安非他明刺激下纹状体背侧释放更多多巴胺,并表现出前脉冲抑制缺陷,安非他明诱导的运动亢进,以及对安非他明的谷氨酸反应也发生改变。这提示纹状体背侧突触前多巴胺合成和释放增加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发展。
第2代抗精神病药的作用机制揭示了5-HT2A受体和多巴胺D2受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它们同时拮抗5-HT2A受体和多巴胺D2受体,除了治疗阳性症状外,还可以降低药物的锥体外系不良反应,并有助于缓解阴性、认知症状[14]。它们对阴性症状和认知症状的改善与拮抗5-HT2A受体使前额叶皮质多巴胺释放有关。
多巴胺D1受体与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工作记忆功能有关,希望D1受体激动剂可用于治疗认知障碍。Wang等[9]的研究采用了一种新型的D1受体激动剂PF-3628,在有工作记忆相关神经元放电和工作记忆下降的老年恒河猴的背外侧前额叶皮质神经元直接应用PF-3628,发现了D1受体激动剂使工作记忆相关神经元放电并改善工作记忆损害,并且PF-3628的有益作用可被D1受体拮抗剂阻断,表明D1受体激动剂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障碍有帮助。
整合的精神分裂症多巴胺假说认为,可以用多巴胺通路的调节失调来解释多数精神分裂症所有症状,特别是中脑边缘多巴胺通路的活动过度(阳性症状),至背外侧前额叶皮质的中脑皮质多巴胺通路的活动低下(认知症状和阴性症状),以及至腹内侧前额叶皮质的中脑皮质多巴胺通路的活动低下(情感和阴性症状)。
综上所述,中枢多巴胺功能参与调节的主要精神活动有认知、动机、奖赏等,与一些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密切的联系,对多巴胺功能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揭示精神分裂症、物质成瘾障碍和ADHD的病理机制和发现新的治疗靶点。